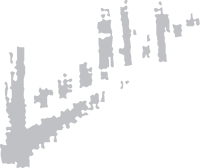不要讓自由從指縫間溜走

REFLEX.CZ訪談
文字:Marek Gregor
照片:Nguyen Phuong Thao
LORETTA LAU(34)於布拉格藝術、建築與設計學院(UMPRUM)快將展開最後一年視覺藝術碩士課程,本來投考了德國魏瑪包豪斯大學(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的她,來到布拉格學習或多或少是一個偶然。 她在香港教育大學畢業後於兩所中學教授視覺藝術科達七年之久,2018年她毅然決定去歐洲留學,在這裡她找到了一個新的藝術定位——政治行為藝術家。這都無可厚非,2019年6月中共政府草擬的引渡法當頭棒喝香港長久以來的法治基礎,該項法案旨在引渡被刑事起訴的港人到中國服刑,直到現在民主抗爭已成為港人的日常。
是甚麼令一位32歲的香港女性來到捷克學習藝術?
畢業之後我在香港兩間中學從事視覺藝術科教師,七年過去我卻漸漸失去教學動力,這並不是因為我對教育的熱情冷卻,而是香港教育制度對學生所施加的壓力使我感到極度沮喪。就個人而言成為藝術家比視藝老師更接近我對自己的期盼,所以我決定出國學習,初時報考了德國Bauhaus的公共藝術與新藝術策略課程,得知未獲取錄後我迅即投考布拉格的UMPRUM。
您七年後重返校園在Jiří Černický的繪畫工作室開始學習,由教師再次成為學生的感覺如何?
一開始我感到非常錯愕,我完全無法理解他到底想我做什麼,總覺得Jiří不太喜歡我,或者是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及語言障礙所致。起初實在是難以適應,過了一段時間他竟然問我:「Loretta你為什麼總是畫畫?你不如試下跳泰國舞?」 然後他做了一些雙手合十等跳舞動作,我看得無名火起:「泰國舞跟我有何關係,難道膚色黝黑的我就該懂得跳泰國舞嗎?」 實在看不慣這種中歐大男人主義,在香港我從來都沒有遇過這種對待。
我還以為Jiří Černicky 是UMPRUM中最著名的女權主義者…
隨後我意識到他想遊說我使用其他技巧或不同的表達方式去創作,而不應局限自己於炭筆或油畫等傳統媒介之中。第一學期的鬱悶促使我急不及待地飛回香港與朋友和家人度過2019年的農曆新年,兩個星期後我帶著活力重返歐洲,當時我完全無法想像一場惡耗將降香港。我開始在互聯網上看到中國正在制定引渡法,人們開始害怕香港法治受損,第一場小型的示威爆發,參加遊行的人數不超過一萬。直到6月9日,即香港立法會對法例進行二讀之前,才發生了重大的轉折點,逾百萬港人上街表示不滿。
與此同時您展開了政治行為藝術表演…
2019年6月3日,六四大屠殺發生三十週年之時,DOX當代藝術中心舉行了一次紀念晚會,是次晚會紀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被殘酷鎮壓的死難者。我僅在晚會兩週前得知捷克著名雕塑家Marie Šeborová剛完成了劉曉波的半身像,並將其聳立於該藝術中心的展覽廳。她也是愛爾蘭國會大廈內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半身像的作者,而哈維爾便是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提名人。其實香港亦曾經出現過兩次劉曉波雕塑,但作者都害怕承認其身份,故以匿名贈出。而那時香港的緊張局勢再次升溫,於是我鼓起勇氣告訴自己要走到劉曉波半身像前進行第一次行為藝術,並電郵DOX可否在該藝術中心演出。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剃光頭以象徵丈夫多年來所受的牢獄之苦,而我為了紀念劉曉波及其他為自由民主犧牲的每一位,我決定作剃頭的儀式,並由另一位香港藝術家黃諾翹所執行。對於我來說,那次表演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在完結後很多人主動聯絡我,關心香港的情況。
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香港或中國所謂的「一國兩制」存在問題?
2013年中國開始明目張膽地擾亂香港的教育制度,香港的教育一直以德育及公民教育為基礎,我們從小就了解「普世價值」、「三權分立」及「公民社會」的重要性,教育局突然想改寫課程及加強學生的愛國意識,許多年輕的抗爭者、學生和教授都對此表示反對,而戴耀廷教授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然而他今年已被香港大學開除了多年來的教席。我們當時已意識到他們想進行洗腦教育,並將我們變成言聽計從的中國公民。但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香港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這是街頭抗爭的因由,首先是反國教,然後是雨傘革命,從2014年8月到12月街上有成千上萬的人群,高峰時每天更有120萬人。
那是什麼結束了2014年雨傘革命?
他們設法通過許多虛假的承諾使大家平靜,無謂的反抗只會拖延普選步伐 。香港人是水中的青蛙,我們沒有意識到鍋中的水越來越熱,在那沸騰的水中感到格外舒暢,最後卻被活活煮死。
當初人們如何看待香港在1997年七月一日從英國移交中國以及五十年不變的諾言?
那時我只有十三歲,但是我記得當晚即使滂沱大雨,英方的告別儀式依然盛大。人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許多人因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擔憂而飛往加拿大或英國。然而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並沒有採取任何明顯的行動去遏制民主,公民自由看似得到保障。人們出入境頻繁,同時香港繁榮依舊,許多人離開了又回來,至少在最初十年許多人對從英國過渡到中國管治下的香港持正面的態度。
這聽起來十分奇怪,畢竟六四大屠殺與主權移交之間只相差八年…
你要知道金錢對香港人的重要性,而且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國際金融中心,在金錢的誘惑下人們容易忘記傷痕。
葡萄牙前殖民地澳門也是中國管理下另一個一國兩制的特區,與香港只隔五十公里的澳門為什麼沒有像香港這樣的大型示威發生?與澳門是賭博天堂有關嗎?
我想這與人們的心態有關,這實在很難說,我不想作出沒被實証的判斷,但比較一下香港和澳門的公立大學數量及質素,我認為這可能與公民教育有關。此外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我們擁有可靠的金融體系,以及其他國家對香港的信任,這使香港人產生強大的自我認同感。
那台灣呢?
從我的角度來看,台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是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雖強,但我對香港能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依然抱有懷疑,大部分人還沒有要求獨立,而只想繼續原本的香港,我很難把兩地作比較,但是我們卻有著共同的目標。
您應該知道捷克參議院主席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最近到台灣訪問…
我十分驚訝,其後看了韋德齊的演講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口頭威脅。王毅揚言要切斷兩國的外交關係,在我看來這像是宣戰的腔調。縱使捷克是一個小國,但畢竟也是歐盟的一部分,中國的論調實在滑稽,當然德國和法國外交部長對捷克的支持在是次事件中亦持重要的角色。
這樣說您不怕自己無法返回香港嗎?
大概吧…我現在主要通過互聯網與朋友和家人溝通,但中國在大陸限制使用Google、YouTube、Facebook之類的網頁,一旦香港的互聯網成為大陸網絡的一部分,我怕之後要下載有間諜成份的中國應用程式才能與父母和朋友溝通…
你會返回香港嗎?
如果我家中發生甚麼事,我還是會冒險回去的,但是現在我沒有甚麼理由要回去。
您認為《國家安全法》是否香港民主法制的終結?
在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中共法律凌駕於香港基本法之上,我的確擔心香港自由即將終結,該法案完全否定了香港的自治權。我們竭盡所能試圖讓國際社會了解香港每日所發生的事情,事件亦廣受國際社會所關注,例如前學生領袖羅冠聰為了安全起見,於2020年7月2日離開香港,而三週前他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抵達柏林時,向德國政府展示香港社會的近況。許多香港人在默默耕耘,有人從事政治游說工作,有人善長文宣,有人在做藝術……許多人出國其實是希望在海外進行另一種抗爭,例如導演歐文傑搬到加拿大居住,他在2015年的電影《十年》中預言香港十年後的境況,但不幸的是這些情況已在現實社會中發生;其次是漫畫家柳廣成,他移居到台灣後致力於政治漫畫創作,以鮮明畫風譴責中國和香港政府的不仁。我實在難評論在香港抗爭,還是在其他地方引起海外社會關注才是更好的選擇,但我相信這並不是自由民主的終結。
2020年6月30日之後,英國向所有在1997年之前在香港出生的公民提供庇護,您認識任何人尋求這協助嗎?
現今香港主流分為黃藍兩派,黃絲支持自由民主,藍絲則支持港共政權,後者是既得利益者,為利益而討好政權,只要有錢他們就看不見殘酷的鎮壓。我認識一位女生,她聲稱由於傳統家庭價值觀以及對繁榮的看法,使其想法與中國政權較為接近,可是現在她卻成為首批飛往英國避難的一群。我很欣賞許多黃絲的態度,他們以僅餘的力量和盼望留在香港,更有很多青年人為自由和民主而犧牲自己的未來,他們真正熱愛自己的土地。
2016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總統米洛什·齊曼(Miloš Zeman)的邀請下訪問了捷克,成百上千的人們慶祝他的探訪,我認識一些反對者受卻到人身攻擊, 那您在捷克有遇到一些中國人嗎?
有趣的是自從我來到布拉格都沒有遇見中國人,最多遇到中國遊客,可能是因為我現在生活在布拉格的藝術圈之間。可是最近我收到一些社交網絡的攻擊,今年六四我在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演出,並以說故事的方式去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的死難者,然後我開始收到一些不懷好意的批評,他們說我是法輪功學員,而法輪功在中國是被惡意描述為邪教的組織,我曾收到類似「你靠哪邊?三八!」的訊息,但我並不在乎網上恐嚇。
您在捷克感受到人們的支持嗎?
我在這裡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例如國家科技圖書館畫廊的展覽策展人Milan Mikulaštik。今天捷克人民過著穩定的生活,我嘗試把在世界另一端的香港所發生的事情一一告訴他們,我希望創作能夠把人們連結起來。三十多年前在捷克所發生的「布拉格之春」和「天鵝絨革命」與香港現狀有共通之處,這亦解釋了為什麼在今次的表演中,我把哈維爾1990年的新年演講,與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的新年演講進行對比。倘若您生而享有自由,請記住曾經有人為您的自由淌血,不要以為自由是理所當然的。